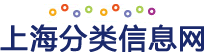原标题:【援疆采风】南疆的水
习惯了上海的连绵阴雨,见惯了江南的青山绿水,带着疑惑,我们从水乡来到戈壁,从江南来到南疆。喀什地区气候干旱少雨,许多地方年均降水量不足100毫米,而年均蒸发量却高达2000~3000毫米,长此以往,不早就成焦土一片?水乃生命之源,那么这生命之源从哪里来?
飞机飞跃天山皑皑雪峰,机翼之下的塔里木盆地边缘,冰冻的河流如一棵高大的白桦,群山之间的小河如枝叶般汇聚成主干。临近喀什,满眼还是一片广袤的苍茫,零星的村庄散落其间。下了飞机,冬日的喀什万木萧疏,入眼仍然是一片土黄色,吐曼河水静静流淌,河边的古老民居矗立高台,不知先民们是如何生活的?
南疆少雨,一年也就那么几场雨雪,每场雨顶多下个一天半天,从家里带来的雨伞从没有用过,喀什地区农村里没有坡顶的瓦房,许多传统老房子的房顶都是平顶土坯的,不需要做防水,即使每年漏一两次雨,重新糊上泥巴即可。前几日好不容易一场连绵的阴雨,已经破了喀什多年的气象记录。这里没有,可能也不需要强大的城市排水系统,对上海来说司空见惯的一场雨,一下子让喀什街头变成水乡泽国,让南疆仿似江南。喀什干燥,葡萄一夜之间变成葡萄干那是太夸张了,不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提示着这里是干旱地区,刚到喀什时晨起鼻子里会有点点血丝,从上海带来的竹笛洞箫没注意保养,很快就开裂破音,脱衣服的时候会有噼里啪啦的静电,刚洗完的衣服基本上几个小时就干透了,而在上海,尤其是梅雨季节洗完的衣服,好几天了,感觉还是没有晾干。这里的墙壁从来不会“出汗”,这里基本上没有被蚊子送过“红包”,干燥的环境里没有它们滋生的污水。到了夏天,也有35℃以上的炎热,但不是酷热,更没有闷热,因为你的汗水还没有淋漓,就已经蒸发掉了。当我弯起胳膊,一会儿肘窝里就汗津津的,一旦伸直,十几秒内马上就干爽了。夏日里也经常看到援疆兄弟们深色裤子腘窝处的白色云斑,估计是屈膝时汗水浸湿,蒸发后留下汗碱。
水,是生命之源,南疆有水。虽然没有北疆的水绚丽,南疆的水也是多彩的,春天里慕士塔格峰脚下的卡拉库里湖黑沉幽邃,白沙山下白沙湖里蓝波渺渺,夏日的叶尔羌河黄流翻滚,秋天高大的胡杨倒映在泽普飘着金子的河水里,又是一簇一簇顽强的明黄,冬日的东湖南湖微波荡漾,吐曼河清澈流淌。夕阳下晚霞返照入水,红柳倒映,巴楚的红海一片火红的灿烂,及至一轮西域明月出于戈壁之上,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峡谷里的塔什库尔干河如喀纳斯河一样碧绿,不同的是,喀纳斯是两岸青山相对,塔什库尔干河水虽如“塔青”碧玉,两岸却是荒凉雄浑的土黄或赤红。春暖花开,大同乡深山里的百年老杏花开朵朵,春风吹拂,落英缤纷,落花有意逐流水,又为如玉碧水增添几分妩媚。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峡谷里河水下泄,平静了一冬的吐曼河水已经开始有些奔腾,清澈的河水已经明显浑浊。下乡义诊,看到乡村里沟渠纵横,渠水平缓清澈,渠水所到之处,白杨挺拔,粉杏开花,麦苗抽穗,葡萄上架。问渠那得清如许,不知源头从何来?
喀什北部是横亘新疆中央的天山山脉,北冰洋的水汽被阻挡在了北疆,落在天山上,滋润着那拉提等青青草原;西边是“万山之祖”的帕米尔高原,即使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也落在了千里之外伊犁的赛里木湖,南边是高耸广袤的青藏高原,印度洋的水汽也难以逾越,东面是万里无垠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浩瀚的太平洋,在万里之外。西南而望,巍巍昆仑山上的皑皑诸峰,是喀什的水塔吗?
喀什近郊疏附县的乌帕尔乡是一位维吾尔族学者的故乡,公元11世纪的时候他就走遍了伊拉克等中东地区,晚年他回到故乡著书立说,撰写了一部不朽的百科全书,去世后安葬在家乡的半山上。在他的陵墓前一棵老杨树拔地而起,根处一眼清泉汩汩流淌,奇特的是,往上十几米外就是光秃秃的荒山,往上爬一会儿,竟然看到两只追逐狂奔的蜥蜴,这些一尺多长硕大家伙好像只能在沙漠里才能碰到。登上山顶俯视这境界分明的盆地,泉水所到之处郁郁葱葱,而在四周山上似火焰烧过,寸草不生。附近的四十眼泉景区,同样山上山后是茫茫戈壁,而山下,几十个泉眼从青草中静静流出汇流成河,水草丰茂,仿若草原。顺着水流我们来到临近村里,小溪入渠,灌溉入田,滋润万物。这不老的泉水,真是传说中这位圣贤的拐杖插入山腰化为白杨,引出清泉,遗泽万世?
夏日某天,从叶城新藏公路零公里出发南行20公里,我们来到著名的宗朗灵泉,远望湖面澄碧如洗,宛如一块巨大的碧玉凝脂,湖边蒹葭苍苍,古柳偃卧,沿山脚长廊上行,灵泉如星,不时有泉水从陡崖腰际涌出,飘落山下,如丝似线。江南的叮咚泉水,总在青山脚下,可以想象山间云腾致雨,雨渗入土,漏入石缝,化为山脚清泉。可这里,陡崖之上却又是茫茫戈壁。望着几百公里外巍巍喀喇昆仑山上的雪峰,看着眼前镶嵌着鹅卵石的砂石崖壁,我似乎明白,或许雪峰上冰川上的冰雪融水,透过松脆的砂石缝隙,从地下长途潜行至此,找到众多的宣泄出口,汇聚成泉?
清泉潺潺流下,汇入山下浊浪滚滚的叶尔羌河。昨夜的暴雨让昆仑脚下的叶尔羌河挟泥带沙,咆哮着奔向塔克拉玛干这个“死亡之海”,最终消失的无影无踪。我的家乡在河南,见惯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在这里,看着湍急的洪流,听着哗哗的水声,我又似乎站在了黄河岸边。逝者如斯夫!叶尔羌河,你来自哪里?去向何方?
驱车进入沙漠腹地,沙丘如黄色的波浪连绵不绝,明暗相间,沙丘顶部已经干透,是明黄色,而底部仍然是含水的暗黄色。车行沙上,轮胎些许下陷,站在沙上,脚下并不松软,挖开表面,下面的沙子仍然是湿湿的,我知道,是水的表面张力把这些沙子团结在了一起,让沙丘更加坚实;表层覆盖的沙子遮挡了强烈的阳光,这些水分避免了“气化升仙”,但它们还是抵挡不了地球的引力,终究会慢慢下渗,汇入地下径流,于低洼处形成一汪清泉,一如敦煌鸣沙山下的月牙泉;或者于平坦之处形成一片湖泊,善利万物而不争,滋养一方土地,承载万千生命。茫茫沙漠里仅有的几场雨如此这般为片片绿洲提供了绵绵不绝的水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我们,是冰山下的来客;巍峨的慕士塔格峰为什么这么洁白?白云是冰山上的常客。强烈的日照蒸腾起每寸土地的水汽,升腾高空,聚结成云,白云飘飘,随风而去,遇见高冷的慕士塔格峰,化为晶莹冰雪,千年万年,形成冰川,日暖雪融,滴滴雪水汇成涓涓细流,一路如学童般奔腾跳跃,来到山谷,又如健壮青年一样孔武有力,奔腾咆哮,冲击崖岸。冲出山口,仿佛沉稳有力的中年人来到平原,滋润万物,最终如温和慈祥的老人一样,百川到海,静寂消失。如此以往,周而复始。而这一切背后巨大的力量便是炽热的发出万丈光芒的太阳!感恩,伟大的太阳!
天下莫柔弱于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水的力量是无穷的,宗朗灵泉边上的水轮不停地把玉米碾磨成粉;玉龙喀什河的激流把成块的和田玉山料由昆仑山中冲出,一路打磨,流落荒漠河床,变成红皮白肉的羊脂玉籽料,正所谓玉出昆岗。南疆缺水,但荒野之中满目是水流过的痕迹。南疆下雨很少,但即便如此,千年亘古的雨水也在处处荒山之上留下冲刷的条条沟壑,奔腾的河水冲击荒原,处处可见坍塌崖岸。昼夜巨大的温差使本不坚硬的火山岩(在南疆好像很少有坚硬的花岗岩)风化成土,寸草不生的山体难以阻挡洪水的冲击,被河水下切后形成峡谷,河水冲出峡谷的阻挡后挟带的泥沙在每个山口沉积,形成大大小小的冲积扇,山口处河水下渗,又在远处冲积扇的底部冒出来,形成汪汪清泉。涓涓细流汇成盖孜河和吐曼河等几条大河,冲出喀喇昆仑山后形成了最大的冲积扇,而喀什古城,就坐落在这个宽阔的冲积扇上。
南疆的土地偏碱性,刚到喀什的时候看着路边的戈壁上一层白花花的碱,就连湖边砖铺的路上都泛出一层白色,初春刚到喀什时还以为是未融化的冰雪。如此的盐碱地只有红柳等耐碱植物生长,不过万灵之主的人类还是有办法,在土地里挖出排碱沟,然后用水猛灌,等盐碱溶解后排出或者渗入更深的土层,上层土壤就可以用来精耕细作。南疆土质松软,地势较为平坦,无法像吐鲁番一样开挖坎儿井,聪明勤劳的人们就开挖一些明渠,引水入田,即使在一些村庄之间的戈壁滩上,高速公路边上,也有一些干渠支渠,如此这般大量的荒漠变良田,雪水滋润万物,养育南疆的各族人民,孕育着丰富多彩的十二木卡姆和刀郎文化。
然而南疆仍然是缺水的,每年春天的下土季节,东风吹起沙漠戈壁上的尘土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土腥味,即使紧闭门窗,桌子上仍会有一层沙土。这个时候多么怀念江南阴雨连绵的日子,多么希望能够有一场及时雨降尘除灰。想起电影《不见不散》里,葛优天方夜谭提出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出一个口子,让丰沛的印度洋暖湿气流吹入塔里木盆地,变荒漠为良田,当时一笑了之。进入新时代,设想中的红旗河工程让藏水入疆似乎不再是梦想。想象一下万里长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穿过横断山脉,绕过河西走廊,流淌南疆,滋润土地,万物生长,宏伟的世纪工程让人热切期盼。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南疆这片热土亟盼党的德泽。万物生长靠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在这伟大的新时代,我们相信在伟大的党英明领导下,南疆这片热土会更加广袤富饶,一定会实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南疆的未来会更加繁荣昌盛。
作者:喀什二院援疆专家、普外科主任戚晓升